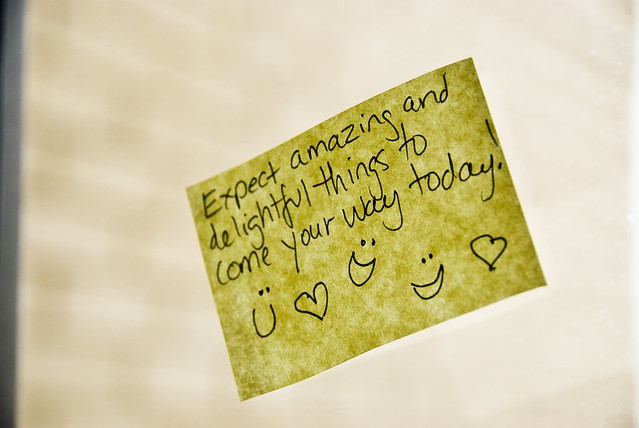|
| Nils Dougan@Flickr, CC BY-NC 2.0 |
匹茲堡的冬天比我想像的暖和不少,目前溫度大約在攝氏零度和十度之間震盪。我的廚藝在克服了頭幾個月的蠻荒時期後,慢慢收歛在電鍋和湯鍋的範圍裡。畢竟平底鍋炒東西又油又麻煩,而大烤箱我也懶得特地打開來用。此際我已能俐落地削切大部分的水果與蔬菜,煮飯的時間也縮短到備料煮好吃完洗乾淨大約一到一個半小時左右。我知道義大利麵該煮多久、配多少醬汁;我知道米水比例怎麼抓;我知道哪些水果可以久放哪些不可以;我知道蒸蛋要加多少鹽;我知道哪個牌子的焙果用電鍋蒸了會糊掉而哪個不會;我懂得如何挑選好的四季豆;我甚至知道綠花菜與白花菜的差別不只是顏色而已。
本已許久不曾喝咖啡,但這週終於還是破了戒。聖誕節前去超市順手買了蛋酒(eggnog),和冰咖啡混在一起驚為天人,於是在期末的推波助瀾之下又重新走進了星巴克。下學期可能就會買個咖啡壺了吧。
我的指導教授寡言而內向,這學期的研究幾乎是在悠悠忽忽中就度過了。期末將屆的這週,我終於想到一個可用的模型來解眼前的問題,但我得在兩週內把它做出來,證明它是對的。如果是平日的兩週理當不難,但期末考也無法輕易放過,接下來的兩週看起來會很難過了。
這學期最大的收穫是讀書,讀了非常非常多中文書。我把從臺灣帶來的閒書看完了三分之二,今天正巧看到《道濟群生錄》的最後幾頁。誠實地說我並不很喜歡《道濟群生錄》,大抵就是不喜歡在哀傷的基調裡抹上五顏六色的樣子,其實段子倒是寫得蠻精彩。
這幾個月來唯一無法真正讀完的書是舊譯本的《玫瑰的名字》,題材硬、譯筆也硬,我看到前幾章(剛到修道院沒多久)就讀不下去,索性丟回書櫃上去。相形之下《時間的女兒》有趣得多得多得多了。
這三個月可說是我近幾年來最快樂的時光。但倒不是最豐碩輝煌的時光。
我沒有什麼研究產出、也沒有文學作品,勉強算得上長進的就只有廚藝與讀書而已。我無法說自己完全不為此感到有點鬱悶,但整體來說,我感到充盈而自由。加諸於我身上的種種束縛,於此地一併地卸下了。我所要顧慮的,就只有我在意與我選擇的事物而已。無論成果如何,我都沒有任何抱怨。
我更細膩地體察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包括我到底有多挑食),更體切地認識自己的缺點(再也沒有藉口了),買自己想要的衣服與書,香水與保養品,家具與書櫃,小烤箱與麵包籃。凡此種種,固然只是微小的趣味,但我終於能過自己的生活,完整地成為「我」的樣子。
除了戀人與摯友以外,我其實並不想念臺灣。尤其是出國前那段暗無天日的時光,此際的我幾乎無法想像當時的自己內耗了多少的力氣才能強自吞下那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傷害。
我本來怕黑。以前若是自己一個人過夜,我一定會在離床最遠的角落留一盞小燈。
來到匹茲堡、住進新房間後,我仍繼續保有這個習慣。直到一個月後,某個夜裡,我躺在床上看著浴室透出的燈光,想了想,起身下床,走過去把燈關掉。
我摸黑走回床上躺下,眼睛適應黑暗後我在漆黑中環視了房間一週。
好。沒有任何會讓我害怕的東西了。
我終於可以安心入睡了。
20111205@ptt2 (#1Et6PT2I)